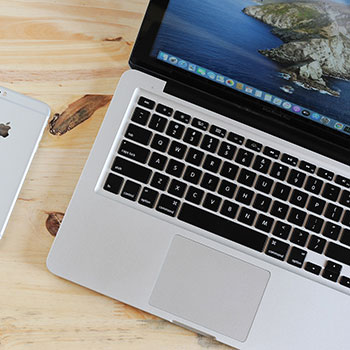克里斯托弗·杰默是哈佛医学院附属剑桥健康联盟的精神病学讲师,也是“静观自我关怀”(Mindful Self-Compassion,MSC)课程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著有《不与自己对抗,你就会更强大》《静观自我关怀专业手册》等著作。
黄小玉是同伴教育机构“海蓝幸福家”的创始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静观自我关怀老师和师资培训师之一,在中国教授“静观自我关怀”课程十余年。
我们需要“柔软的自我关怀”来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重建与自己的关系,建立稳定的内在价值感,也需要“勇敢的自我关怀”来做出正确的行动,在益愈艰难的世界中获得前行的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将“静观”和“自我关怀”两个概念整合起来应用于心理治疗的先行者,“静观自我关怀”的方法是如何提出的?这两者的整合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托弗·杰默:我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长期专注于焦虑症的治疗,而我自己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经受着对公共演讲的焦虑。我坚持做静观练习,尝试冥想、横膈膜呼吸法、剧烈运动,各种各样的办法都于事无补。最后,我拜访了一位冥想老师,她告诉我,我只是需要去爱自己,她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指导,让我对自己说一些善意的话,“愿我平安”“愿我健康”“愿我自在”。
在2006年,这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心理学者们从不这样做。我们总是尝试从问题中脱身,而当我们想要摆脱问题时,事情只会更糟。伤痛在抗拒中持续,在接纳中疗愈。我意识到公共演讲的焦虑并非是焦虑障碍,而是一种羞耻障碍,我无法接受自己站在讲台上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我无法接受同事认为我无能。羞耻感的深处是对被爱的渴望,当我关怀自己,我的心才得以休息。
2010年,我和克里斯汀·内夫(Kristin Neff)一起创立了“静观自我关怀”课程。研究“关怀”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有进化论的、生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我们的方法则是建立在静观练习的基础上。1979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开启了静观在临床上的运用,基于科学而非宗教的静观训练开始出现。2003年,克里斯汀·内夫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自我关怀的论文,奠定了自我关怀的三个组成部分,并制定了测量自我关怀的量表。“静观自我关怀”的提出建基于两个领域长期以来的科学研究。
静观自我关怀并不是一种心理疗法,而是帮助人们发现和创建资源的方法。心理治疗侧重于减轻痛苦,而资源关注的是增强力量。静观是对每时每刻的体验不加评判的觉知和接纳,自我关怀是对我们自身的广阔而温暖的爱意。静观关注的是体验,它问的是:“我正在经历什么?”自我关怀关注的是体验者,是人,它问的是:“我需要什么?”可以说,静观自我关怀是“有温度的静观”,两者能够很好地相互补充。

克里斯托弗·杰默: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你这个蠢货!你以为你是谁?你怎么做了这种蠢事!”我们感到痛苦,于是把自己藏起来、反刍痛苦、捶打自己,我们的想法从“我感觉很糟糕”变成了“我是个糟糕的人”。
但自我关怀使我们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一个懂得自我关怀的人会说:“此刻我感觉很糟糕,我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后悔和自责,我太差劲了。但我不是唯一有过这种感受的人,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形,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愿我接纳原原本本的自己,愿我学着爱自己。”这两种回应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语言文字,而是态度和语气的差异。不是批评、攻击、羞辱,而是尊重、理解、陪伴。当你问“我能够做什么”时,答案将是你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去做,这些话语都存在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善意、友善、温暖和鼓励,这就是自我关怀的本质——一种全然不同的态度。
人们很难自我关怀,这一方面是一个生理学现象,当我们感到痛苦或恐惧时,我们处在生理学上的压力状态,我们感到威胁,我们要么攻击,要么逃跑,要么冻结,而关怀的基础是感到安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所有文化都告诉人们不应该自私,人们往往认为自我关怀会陷入自私和自怜,让人失去动力、变得软弱、自我放纵。然而,8000多篇自我关怀的研究文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自我关怀一再被证明对心理健康、减少焦虑和抑郁、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改善人际关系是有益的,懂得自我关怀的人有更强的情绪韧性、更强的关怀他人的能力和更强的实现目标的动力。
自我关怀的核心是态度,是善待自己的意图。生活中,当你对自己感到不满、感到挫败的时候,可以学着提出三个问题来培养这种态度和意图:“我需要什么?”“如果我的朋友处于同样的情况,我会如何对待他?”“以前遇到的困难中,我是如何成功关怀自己的?”这三个问题就像火车的引擎,能够将整辆列车拉向自我关怀的方向。
克里斯托弗·杰默:文化的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但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与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之间的差异,比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巴西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
一般来讲,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更容易学习“自我关怀”,即使在有集体创伤的情况下,因为人们更注重群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更紧密,并且在群体活动中互相帮助,他们善于关注、理解和回应别人的需要,从而练就了强大的“关怀肌肉”。我们学习关怀自我的方式,就是用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来反过来对待我们自身。当我们懂得关怀别人时,关怀自己也就不难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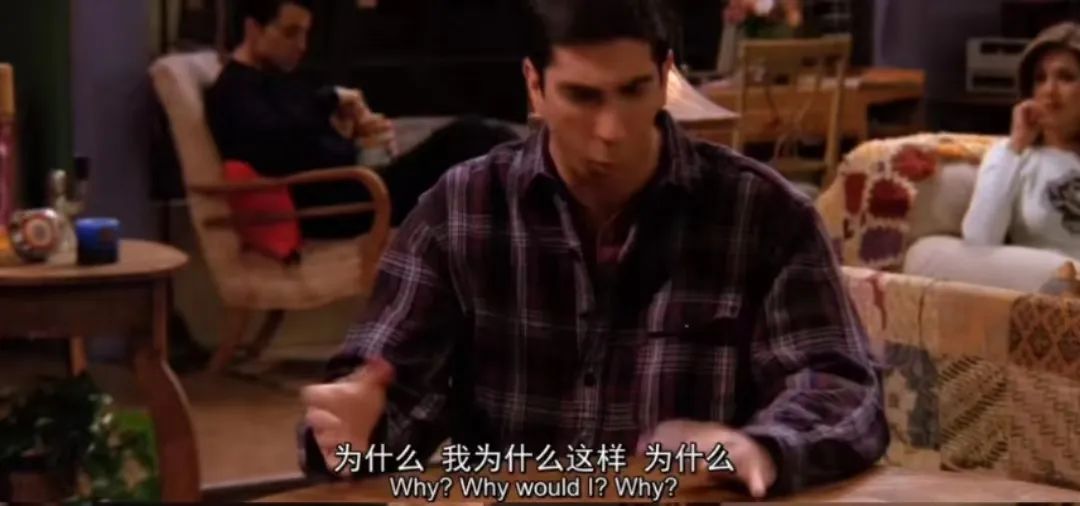
当我们批评自己,我们会感到孤独、与他人分离,认为“其他人都过得很好,我是唯一无可救药的失败者”。
自我关怀让我们学着意识到,我们此刻所经受的痛苦是人人都有的,生活的挑战和个人的失败都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被允许的。
自我关怀打开了我们内心爱的源头,让我们可以按自己需要的方式、7×24小时随时随地爱自己,这叫自给自足。
没有人会真正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无法真正爱别人,这是为什么自我关怀是雪中送炭。
他们在一个点上看问题,把问题归因于自己的错或者别人的错,分别给人戴上受害者或者施害者的帽子。
自我关怀除了温暖有爱,也是智慧的练习,它的核心三要素之一——共通人性——指的就是不要把你的问题当成你一个人独有的问题,你的问题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在经历或曾经经历,你所有的痛苦都有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你所有的情绪都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
因为缺爱而恐惧、而焦虑,因为缺爱而羞愧、而愤怒,因为缺爱而悲伤、而压抑,都是人类共通的路径。
如果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自己,也就能深刻地理解他人,从而在人际关系中更加游刃有余,我们能守住自己的边界,也能照顾他人的需求,我们不为难自己,也不强求他人。

在高度竞争的优绩主义社会,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的生产力、由我们在社会阶序中的地位来衡量的,我们是外部力量的奴隶,丧失了内在的自由,依赖于外部认可而形成的价值感是不稳定的。
善于自我关怀的人有更加稳定的内在支持,他们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笃定自己的价值,他们的动力来自正向的激励而非负面的批评,因而有更强的内驱力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现在的成年人和青少年都面临激烈的竞争,社会比较普遍的是强调“自尊心”,不过这其实带来了一些问题。
其次,自尊带来的价值感是基于外在表现的,比如“好成绩=好孩子”,如果下次没考好,就不是好孩子了。
当我们向外寻求对自己价值的确定时,就会到处想要证明自己,从而加剧竞争、忽略共赢,忽略了欣赏其他人的天赋才华或能力,也没有时间欣赏自己。
善于自我关怀的人看自己,就像最爱自己的人对待自己一样——就像永远站在你这边的爷爷、奶奶,他们不管你考多少分、工作好不好,只要你回老家,就给你留着小时候爱吃的东西,用花手绢包着放在枕头底下要拿给你,满心满眼都是你,他们爱的是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人。
自我关怀让你在任何一个状态下,都能靠近和陪伴自己,不是只有成功的你才会被爱、才有价值,落魄的、不堪的、挣扎的你,也同样值得被爱,也有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自我关怀是会让人更加安于现状,还是更加追求卓越?如何能够让我们形成更强的内驱力?
自我关怀本质就是爱自己,不仅是在遭遇挫折、情绪搅扰的时候爱自己,或者日常生活中给自己滋养和赋能,也有面对人生长河、更深切的爱自己。
最深切的爱自己,就是按自己的意愿来活,活出更高版本的自己,善用上天、时代、父母以及周围的人和事给我的天赋和资源。
自我关怀帮助我们一次次回到自己,了解自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断明确自己的目标,而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出于压力或恐惧去服从或讨好,而是我喜欢这个事,出于热爱去做。
大多数人安于现状,是因为没有对“更好的自己”的向往和相信,或者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更多的人是因为害怕失败,害怕被别人批评、否定,所以退出、逃避、不参与。
完美主义的人关注事,一定要达到某种程度、做成某种样子才算成功,比如必须100分、第一名,不然就一文不值;
在没做到的情况下,他们要么批评自己,要么抱怨他人,还可能自暴自弃,用对抗、逃避或陷入的本能方式来回应。
追求卓越本质上是自我关怀,他们的关注点是人,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我可以尝试什么、我和自己比有什么进步。
如果阶段性成功了,他们欣喜、庆祝,如果不成功,他们理解面对这种情形的困难情绪,可以接纳自己暂时的不成功,依然愿意陪伴自己、相信自己,从而更加敢于再次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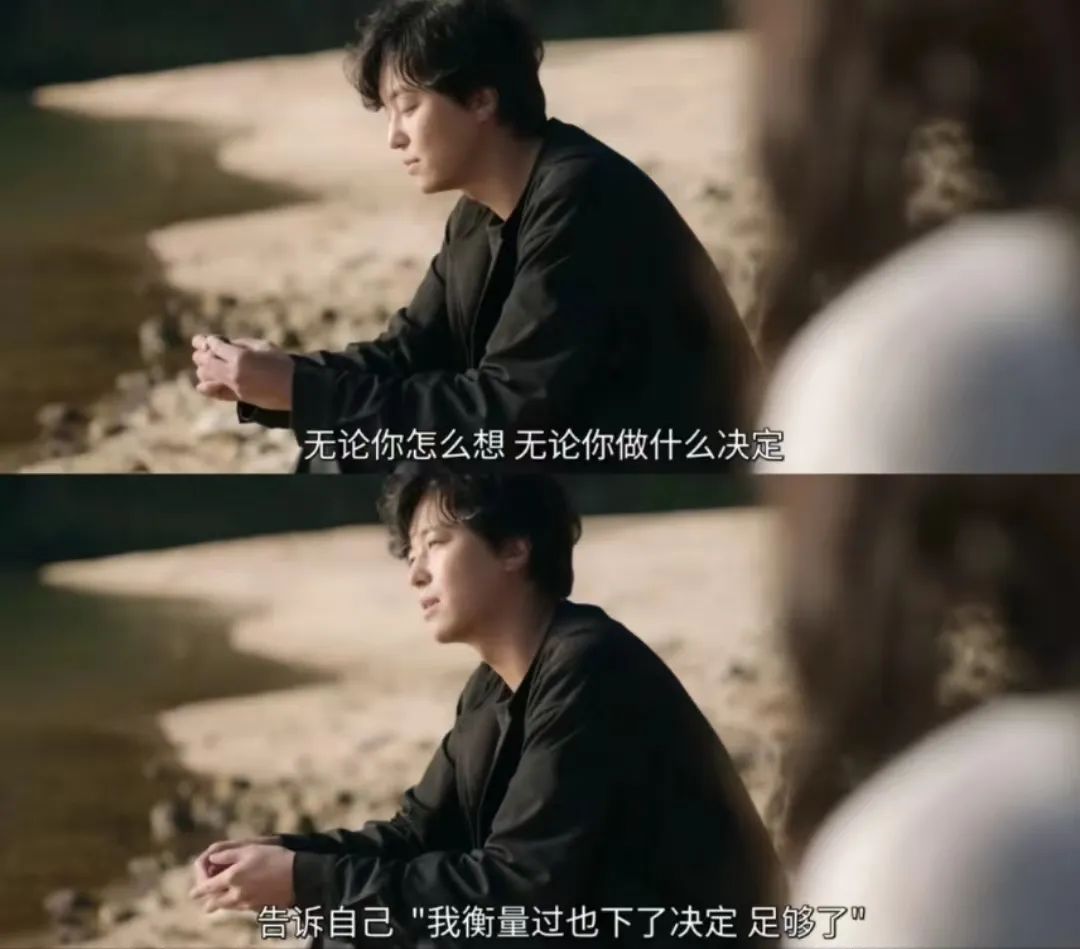
自“静观自我关怀”提出15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人们经历了疫情、战争与经济下行,“静观自我关怀”方法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
,通过身体的安抚、情绪的安慰、对自我感受的接纳来实现关怀,接纳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保持现状。
尤其当我们的生活中充满阻碍时,我们遭遇失业、罹患病痛、孩子在学业中挣扎,世界变得越来越难,我们如何才能带着能量与热情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