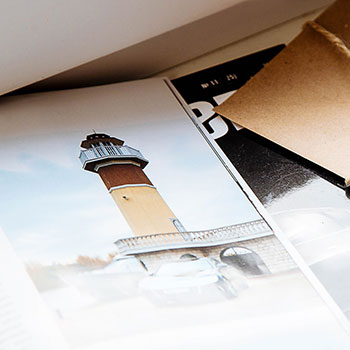这就是为什么外交政策的顶尖专家推测德国的和平统一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太可能实现,却不得不在庆祝的烟火绽放在自由柏林的上空时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美国在1945年发明了核弹,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员却花了10年时间进行爆炸测试才对电磁脉冲有了更好的理解。
而公众直到1962年才知道电磁脉冲的存在,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次测试导致数百公里外的夏威夷路灯灭掉,电话故障,科学家们已经猜想到会有这种效应,但影响范围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科学主题本身就是要根据一套细致的规则不断进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理论会被更优的理论替代。
如果政策专家能未卜先知或无所不知,那政府就不会陷入赤字,战争也只有在疯子的煽动下才会爆发。
有时候,专家的失误也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但这种失误受到的对待与那些劳民伤财的错误却相去甚远。
他们并没有想着要降低卵巢癌的风险——但很明显某些控制生育的药物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效果显著。
当然,如果生育控制药物只会增加癌症风险,我们就会扼腕叹息又一次科学的失败,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在半个世纪前无人知晓,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到了2017年,只有10个国家跨过这道门槛,其中有一个国家——南非——还曾经声明放弃这种武器。
)[8]肯尼迪的预测是基于最佳专家团队的建议,也不是不可能或不合常理的,但是,在这同一批专家所提倡的政策协助下,未来核武国家的数量降低了。
如果我们接受专业人士的工作所带来的裨益,那也得接受不那么完美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定程度的风险。
有些情况下,当艺人——当然是他们那个领域的专家——把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开始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发表看法,这就是明显的跨专业入侵了。
一个专业人士如果专业学识深入,但知识面窄,那在自身领域以外的问题上,也就未必比其他人更有才学。
强调预测就是在破坏科学的基本规则——科学的任务是解释,不是预测——而社会作为一个客户要求预测多过解释。
就这一点而言,专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无论学者强调过多少次,他们的目标是解释世界,而不是预测离散事件,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还是青睐预测。
)这就是专家和客户之间自然但无法克服的紧张关系,大多数人喜欢预测问题并加以避免,而不是事后解释。
他们一方面希望民众不会抓个现行,另一方面则希望同行不会注意到,或是把他们的欺骗归类到诚实的错误。
如果有研究者或学者伪造研究成果或冒充专家的人谎称自己获得某个领域的资格证书或执照,那就是明显的行为不端了。
[科学家用一个非常全面的缩写“FFP”来形容这种行为,意思是“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 ication)或抄袭(plagiarism)”。
]这种行为不端可能难以辨别,因为这需要其他专家找到线索,普通人不具备剖析科学研究的能力,最多也就是可能凑近墙上的书仔细看看是不是真的。
现实中的“超级伪装者”弗兰克·阿巴内尔(Frank Abagnale)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过这种大胆华丽的造假[之后事迹被拍成电影《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阿巴内尔的行为包括冒充飞机驾驶员和医生。
还有一种更普遍但更微妙的欺诈,就是有些人的确是专家,但他们用伪造的荣誉或夸大其词来加强资历。
他们也许会声称自己是某专业协会的成员,或参加过某专家小组或研讨会,或是受过勋或获过奖,或是其他伪造的修饰包装,这些人通常只有在一些契机导致其他人去查阅他们的记录时才会被抓包。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对撒谎和欺诈的法律制裁以外)专业组织、学术基金会、智库、学术期刊和大学保留对这种恶意渎职的一些最严厉惩罚。
虽然很多教授的合同里都有“反公德行为”条款,但21世纪的社会准则已经把标准降到很低,一个教授在课堂或私人生活中的行为几乎很难触及那条红线,以至于让学校终止任期。
像对学生进行人身威胁或完全不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这种明显会导致解雇的过错可能还是会触发解聘的后果,但就个人行为而言,通常几乎所有情况都会被忽略掉。
学术自由保障了人们有权表达不受欢迎或与众不同的观点,但这不是给制造马虎草率或刻意误导人的研究开绿灯。
比如,科罗拉多大学解雇了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一个把纽约“9·11”受害者比作纳粹的讲师——他们解雇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近人情的蠢货,而是因为他的评论引发人们去关注他的“学术著作”,结果发现其中有部分抄袭。
丘吉尔就解职事件提起上诉也是基于这一点,辩称他的抄袭是一些无心的过失,只是因为他持有争议的观点,才被大家发现。
一定要发生把双子塔遇难者称为“小阿道夫·艾希曼”(little Adolf Eichmann)这样的事,就像丘吉尔所为,才能去仔细查阅一个教授的学术著作?
2014年的同性婚姻研究,包含了大规模数据造假,是一个特例,并且因为其结论的潜在政治影响力而受到大量关注。
大多数学术研究都不会像一个宣称可以说服人们走出恐同情绪的研究那么有趣,所以也不会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2011年,一名博士后研究者拿着美国政府的拨款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研究,结果被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细胞生物学研究方面造假。
这个研究者同意三年内不接受任何联邦政府拨款,但在他的不端行为被发现之前,他的文章已经被其他科学家引用了不下150次。
还有更戏剧化的案例,一个名叫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医生发表了一个把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的争议性研究,2010年在英国被吊销医生执照。
英国医疗部门表示吊销韦克菲尔德的执照不是因为他支持了一个充满争议的主题,而是因为他违反了很多基本的科学行为准则。
英国医学总会(UK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发现韦克菲尔德“曾经在未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儿童进行侵犯性研究,侵犯了儿童的临床利益,没有披露经济利益冲突和不当资金”。
比如,主要的艾滋病否定论者之一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虽然面临指控说他涉嫌学术行为不端,但还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校就这项指控在2010年对他展开了调查并驳回了指控。
说起来可能会对普通人聊可安慰,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行为不端在发生,是因为所有领域的科学家都供认不讳。
2005年的一项调查问到科学家是否有过不诚实的研究行为,大约2%的科学家自认至少伪造、篡改或“修饰过”一次数据,14%的人说曾目睹同事有过此类行为。
当被问及严重行为不端,但还没达到完全造假这样滔天大罪时,1/3的受访者承认他们涉及不那么明显但还是值得商榷的行为,比如忽略与自己观点冲突的发现。
大多数学术期刊的文章撤回都是因为一些冷门话题研究中的不起眼错误或失实叙述,这与人们在《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或《局内人》(The Insider)这样著名的电影里看到的大型欺诈的戏剧性故事不同。
具有最高影响力的科学和医学期刊——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文章撤回率较高。
不是为了防止抄袭——虽然的确有这个作用——而是让同行能够跟随它们的脚步,看看他们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
普通的同行互审不包括重做实验,而是推荐人会在假定论文符合基本的研究标准和流程的情况下来阅读。
当然,像化学或物理这样的自然科学似乎更主张复制的要求,而像社会学和心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依靠的是受试者,因而也更难复制。
如果有人说某种塑料在100摄氏度融化,那其他任何人只要有同样的材料和一个本生灯,就可以查证这个发现。
正如《》2015年所报道的,一项试图复制100项研究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其结果发表在三个顶尖的心理学期刊上,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结论都没能经受住重新检验。
这项分析是由心理学家完成的,其中很多人都是自愿花时间来复核他们认为重要的著作……经审核的研究被视为核心知识的一部分,科学家借此来理解性格、关系、学习和记忆的动态。治疗学家和教育者依靠这些发现来引导决策,但既然这么多研究自身都有问题,那这些著作背后的科学依据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13]
在很多案例中,问题不在于在重做研究的时候导出了不同的结果,而是这些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结论也许是有用的,但其他研究者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重做这些人类调查。
另一群学者随后又检验了这个调查——毕竟科学就是这样运转的——并得出结论,用哈佛学者加里·金(Gary King)的话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甚至不负责任”。
金指出,当复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应该让学者“魂牵梦萦”,“那要说所有社会心理学家都在胡编乱造就不对了”。
Slate网站撰稿人丹尼尔·恩贝在2016年报道了一组生物医药研究,这些研究出现了与心理学研究同样的“复制危机”。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有欺骗性研究,也有只是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个主题太庞杂了,很难切入,但学术界“复制危机”的源头不是只有纯粹的欺诈,还有完美复制在物质和时间上存在的限制,以及其他问题,比如对拨款的监管不足,学术机构有发表作品的要求(无论多微不足道),这些给研究者造成了巨大压力,学者们的论文或研究一旦出版,往往就会把从前的作品打包装箱,扔到一边。
社会科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尤其难复制,因为它不是基于实验流程,而是专家对独立作品和事件的解读。
我们无法反复重演1962年10月发生的事情,所以一个作者检视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后果并写出文章,呈现的是一个专家对一次历史事件的分析。
贝里尔在书中声称揭穿了一个关于拥枪思想的谬论,据他说,美国人拥枪的思想不是植根于早期殖民时代的经历,而是受近一个世纪后的其他影响形成的。
这个研究本来不会被人察觉,但因为探讨的主题是拥枪,控持者和拥枪团体立刻就贝里尔的观点选边站,故而引来细致密切的审查。
其他学者试图找到贝里尔研究所依托的信息来源,但他们的结论是贝里尔要么是误用了信息,要么是杜撰出来的。
埃默里大学也展开了调查,发现贝里尔的错误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能力不足,但还有一些是学术诚信的问题,这一点无可回避。
2012年,一个名叫戴维·巴顿(David Barton)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书。
)他的书赢得了保守派领袖的赞誉和支持,包括2012年总统参选人麦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和由历史学家转型为政治人物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巴顿在书中说,现代历史学家不仅污蔑了杰斐逊的私生活,还忽视了他的很多思想其实是支持现代保守派观点的。
考虑到杰斐逊是欣赏法国大革命的,而且他后来与自由主义者结盟(这与他的保守派死对头约翰·亚当斯正好相反),这个观点非常大胆。
大多数专业学者都不理会这本书,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就是一个业余历史学爱好者和一个非学术的宗教出版社的合作产物。
这本书的准确性很快就受到质疑,提出质疑的不是某个研究型大学的无神论自由主义者,而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型基督教学校格罗夫城市学院的两名学者。
这本书后来被历史新闻网(History News Network)读者票选为“最不值得信赖的纸质书”,但更具毁灭性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商认为这本书实在是漏洞百出,所以终止发行。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兼法学教授加勒特·埃普斯(Garret Epps)对这一事件做出尖刻的批评,他说:
如果有一组研究集结起来得到一种药物或一种治疗方法,而某一项研究隶属其中,这个研究本身也会触发一连串的研究来审视相关的安全性和效能。
即便一个学者因为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受到政策圈的关注,他/她的影响力也不是由科学复制作品的可能性决定的,而是由作品所提出的观点决定的。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任何单项研究,如果没有其他专家的再次审查,鲜少会影响到普通公民的生活。
就像一组复杂的方程式中如果早早埋下错误,后面的计算就会陷入困境,欺骗或行为不端会耽搁整个项目,直至有人发现是谁搞错——或刻意欺瞒——事实。
当然,如果这样的事情公之于众,随之而来的就是行为不端的范围和影响这一类法律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项目花的是公众的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