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是人类的敌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至少8000年。医学的战法,无论攻与守,无论整体攻防还是局部战争,无论医疗保障体制还是防疫措施、个体治病,都到了有意识地好好总结反思的时候了。晋后中医的退化、中西医之争都可以用战法来鉴别衡量。在战法之中,《孙子兵法》是举世公认的“至真至大论”。我们就依据孙子兵法13篇来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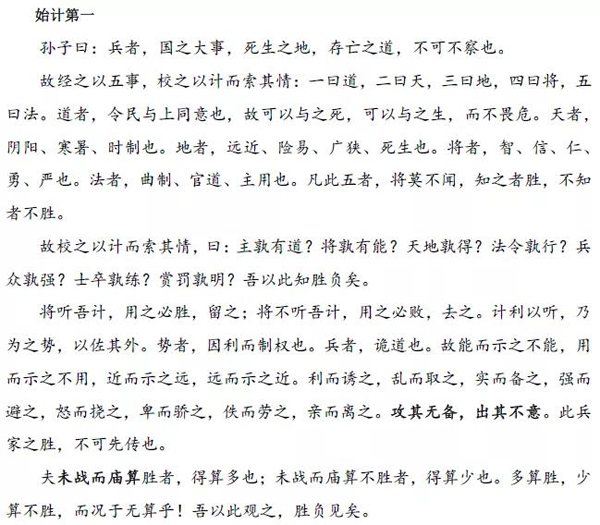
《始计》相当于总体方针。“医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样表达也很准确吧。“经之以五事”,“道”为第一;天地人为第二;制度类“法”为第三。《始计》就整体攻防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未战而庙算。
医疗支出占各国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美国、北欧国家等约占20%;英法德意等约占15%左右;而我国约占6%不到。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效果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中国这个投入少医学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成功控制了疫情;然而意大利的医疗体系被冲垮;英国、瑞典等选择不抵抗“自然免疫”;美国也是实质上的不作为。新冠可以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撕开了发达医学体系的伪装。中国现在的国力当然不能只用GDP衡量,然而即使时代也战胜了多次疫情,包括几千年的血吸虫。存在即合理,如果“未战而庙算”,显然首先是因为“法”的差别,也就是医疗制度、医药体系的差别。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立法实质是3个“垄断”,包括医药研发、试验、批准程序的供给垄断;医药市场即行医制度的需求垄断;医药结算即保险市场的价格垄断。垄断的结果就是费用高、隐性腐败严重,同时最大程度地压制创新。美国保险集团与医药巨头已经占据了最大GDP,已经到了极限,如何再扩大投入于民众健康?这是特朗普撕毁奥巴马议案的决定性原因,也是各国对新冠状病毒选择放任的决定性原因(当然可以人为制造各种帝国理工教授的科学计算依据之类)。时代充分重视广大农村、充分发挥简易中医药的作用;习主席明确指示要求中医药必须加入抗疫的人民战争。中医药的廉价、简易、千年经验以及治疗思路都发挥了现代医学不可能达到的作用。
张仲景为了抗疫研发了边角陈粮+野菜汤,治病用的药材也没有昂贵的山珍海味。简化医生培养程序,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赤脚医生”制度。无论是太守视角还是天子视角,都得“庙算”。对于单个的病人,他(她)也是家庭的一部分,一人治病、全家破产岂能叫仁者仁心。许多病本身医学科技能力有限;各种病的治法也有多种方案,不能为病人“庙算”,患者如何安心治病?心不安,慢性病、重病如何能治愈?
印度这个贫穷的人口大国,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不保护西方医药集团的专利垄断(仿制)+多类科技集成创新降低成本。因为科技园行业的特点是善于便于科技集成,因此笔者一直在关注印度的班加罗尔科技园如何培育出世界最大的医疗集团“那罗严”(Narayana Health),那罗严的成功尤其是低成本有效性,不能简单理解为无专利药,而更应该发现打破垄断的科技创新,那罗严心脏手术的费用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中医药本是完全开放性的,历史上没有也不需要医疗准入。实际上记载的几乎所有“名医”都是半路出家或者自学兼职。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制度恰恰把西医的垄断学会了。当然不可能再创新。
所以,新医学的未来改革,首先是“法”,即医疗体系的改革。用科技创新+科技集成降低成本、提高疗效。医院是公立、私立、个体并不最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走西方医药集团垄断+保险垄断的老路。这个三重垄断医疗立法的必然结果,就是病人家庭无力承担,国家医疗财政早晚会如瑞典、美国不堪重负。
以上三篇都是讲战法。《作战第二》先讲明了战而不能胜的严重后果(败就不用说了)。表面后果是费力+费钱,“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相当于西医路线的“anti”战法,研发各种武器弹药对攻。然而真正的悲惨后果却是必然的并发症,比如“炎症瀑布”。因为身心是一个互为一体的系统,打针吃药手术失败后果不是仅仅局限于病灶。“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如果要避免这种后续反应,就要做到“尽知用兵之害”,而不能只看到“用兵之利”。中药基本都经过了千年以上的验证,而目前常用的西药基本不过几十年。无论老鼠还是人体试验,从逻辑上就能知道很难验证10年20年后的“诸病乘其弊而起”。如果再夹杂商业利益,特别是长周期大成本设计+法律保障的垄断门槛,客观性更加存疑。中药当然不能代替新药创新,但是中药按照先无过再由浅入深、边用边调的用药路线,比统一用药的大规模标准化商业模式显然更加“能善其后”。
顺着这个逻辑,《谋攻第三》从策略上提出开战之前,最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治未病”。真要动手,也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好先按摩调养,不得已才用药用针,“其次伐兵”。严重到专家会诊,就是围城强攻了,“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当下医学,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进步,不断地打败一个又一个“疾病”,但是病越治越多,慢性病等系统性疾病用药总有效就是治不好,为什么?孙子告诉你答案:“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西方医学与战争策略的弱点就是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战术胜利,却会输掉整个战争,比如拿破仑、希特勒。这就是毛主席带领贫穷落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志愿军先后“打败”不可能打败的日寇、美帝的原因。笔者本人自治痛风,也正是按照“上兵伐谋”,先去思虑改变心态;“其次伐交”,通过高尔夫、麻将改变工作生活社交状态;最后调整饮食,勉强算“其次伐兵”吧,因为药食同源,并不用专门服用别嘌醇等,再退一步,宁可用“东革阿里”冷萃取胶囊一类的保健品去尿酸,也好过化学药。如果严重到迫不得已,也是层层布防,逐步加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与中医的平衡调节不同,西医的治病方法是与生命对抗。西药的问题并不是毒副作用,而是被忽略的“anti”,是策略与路线。西药基本是“毒药”,一般分类:消炎药(anti-inflammatory)、抗生素(anti-biotic)、止痛药(pain-killer)、退热药(anti-pyretic)、止吐药(anti-emetic)、止泻药(anti-diarrheic)等多种。“anti”的定义就是:对抗、敌对和竞争。对抗医学,必然会因为对抗疾病而与病人的生命对抗。
对抗医学,类似于欧洲的决斗或者亚述帝国流传到希腊、罗马的方阵对抗。靠抗生素、技术与外科手术的威力消灭对等的敌人。这个打法显然经不住日耳曼人、匈奴人的背后流动骚扰;在更强大机动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对于鼠疫、天花、流感、新冠也只能等待自然选择。
不可否认抗生素与激素都是伟大的发明,也不能否认大规模滥用也有中国医学界自身的不足。然而更重要的是,缺乏系统性与长周期性不是某个激素的问题,而是整个策略或整体路线的问题。西路军的红军战士不可谓不英勇,路线错误就是最大的悲剧。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不可谓不专业,如果路线错了呢?笔者生于医学家庭,他(她)们选择做一位学业辛苦、常年无假、生活平淡的医生职业都是内心充满仁者仁心的可爱的人,笔者本人长期从事科技创新工作,广泛涉足各类前沿科技,包括各类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这些经历与信息不断地在提醒刺激我的内心:整个人类应当反省了。
青霉素本身就是一种细菌,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在有青霉素存在的地方就没有其他细菌的存在。就和养“蛊”一样,把各种有毒的虫子放在一起,看看谁能活下来,就知道谁的能力大,这都是一类的战力对抗的思路。然而弗莱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1941年前后英国牛津大学霍华德·弗洛里与生物化学家钱恩实现对青霉素的分离与纯化,并发现其对传染病的疗效, 美国药企于1942年开始大批量生产。这种新药对控制伤口感染非常有效,迅速扭转了二战盟国的战局。青霉素同、雷达并列为二战中三大发明。战后金霉素、氯霉素、土霉素、制霉菌素、红霉素、卡那霉素等相继发现。1956年,礼来公司发明了万古霉素,被称为抗生素的最后武器。抗生素能选择性地直接作用于感染菌体细胞, 具有选择性抗生谱。对细菌类感染,包括伤口化脓、肺结核、严重腹泻等人类20%的疾病(或一半感染性疾病)都是革命性的。然而,除了药物过敏,更多系统性、长期性后遗症逐渐暴露,而且基本都是围绕最重要的三阴“肝脾肾”。“毒药”本身要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对形脏的伤害还可以算作利弊取舍(包括肝肾功能、胃溃疡、肠道菌群失衡等),而对三阴“藏”的伤害,似乎只有中医的大寒伤阳气、进而伤肾可以解释。如, 小孩使用了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链毒素、四环素等成为聋哑儿童,影响牙齿和骨骼的发育等。成人可以引起耳鸣、永久性耳聋、骨髓造血系统毒性反应、脑脊液损伤、肝肾毒性反应等等,氯霉素、灰黄霉素和某些抗肿瘤抗生素有致突变和致癌作用等。
人类也没有想到抗生素会培养出“超级细菌”。只有抗生素可以产生耐药性,中医药使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中药并不专门针对某个病或某个细菌。按照对抗哲学,微生物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就像人体一样会自卫、防御、反击,最后就是耐药。也就是说“超级细菌”是必然出现的,这个对抗永无尽头。
激素类药物可以更加明确地定义为是一种透支性的耗用“先天之精”的“特效药。”广义的激素类药物包括性激素、 孕激素、胰岛素、生长激素等;狭义就是通常医生口中一般所指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糖皮质激素(GCS),又名“肾上腺皮质激素”,是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一类甾体激素,可人工合成。主要为皮质醇(cortisol),具有调节糖、脂肪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和代谢的作用,还具有抑制免疫应答、抗炎、抗毒、抗休克作用。往往用于抗生素所不及的病症,如SARS、败血症等,具有抗炎作用,称其为“糖皮质激素”是因为其调节糖类代谢的活性最早为人们所认识。
因为透支肾精,激素类药物对很多全身性疑难重症往往很有效,如各型重症肝炎、慢性肝炎;带状疱疹、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等;支气管炎、哮喘、非典、新冠等;红斑狼疮、风湿性及类风湿性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等;病毒性角膜炎、病毒性结膜炎、过敏性鼻炎等。虽然非典中造成了很多病人脱发、骨坏死等典型肾亏后遗症,在2020的新冠疫情中,仍然是争议很大的常规药物。糖皮质激素在抑制炎症、减轻症状的同时,也降低了机体的防御功能。GCS刺激骨髓造血功能,但却抑制白细胞功能,使淋巴组织萎缩减少淋巴细胞数。GCS能提高机体对毒素的耐受性,即有良好的退热作用,但不能中和内毒素,也不能破坏内毒素,对外毒素亦无作用。长期大量应用引起的不良反应,如满月脸、高血压、糖尿、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降低、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伤口愈合延缓、抑制儿童生长发育等等,严重的相当如致残。
另一类药物,如“胸腺肽”,我国也在广泛使用。“胸腺肽”能调节和增强人体细胞免疫功能,用于治疗各种T 细胞缺陷病与免疫性疾病,本身确实能补充成年人胸腺的退化,可以说与中医的打通冲脉思路一致(后文三焦详述)。然而仅仅2003年至2011年,国家中心共收到胸腺肽注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5459例,其中严重病例1326例,占24.29%。严重不良反应主要涉及全身性损害(93.74%),包括过敏样反应、过敏性休克、高热等。增强免疫的药物其严重不良反应均与过敏相关,实际证明人类妄图以单项药物修补系统的努力是不成功的,也可以以此预测干细胞注射的未来。
老子强调的“知”而不病,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是典型的只研究自己的特效药,统一用于各类同病的不同之人;“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就是误诊+药性不明,既对治病无益,反而毒害病人,“不知知”的过度医疗就是例子(案例太多,专门研究也很多,造成的医疗事故医患纠纷越发严重)。
西医科学关注于“疾”,各类手术技术与抗生素等善于外治。而涉及内病,往往系统性,多因性,外治如能成功,从逻辑上就需要更多更多学科加入,更细分分工,更微观全面检测,等等,就是“精准医疗”了。这是一个想像中的理想状态,一旦通过人工智能协助实现,人立刻就成为“上帝”。那么,还有“人”吗?外疾易疗,内病难消。“不知知,病”。医患之病,根在无知而自以为是。医疗在全球都是难题(包括美、加、法及北欧等),恐怕要从现代药医系统找病根。做的好的日本,恰恰是既重视科技研发,又坚持东方医学。医药占了20%的社会成本,又集中于慢性病、系统病、癌肿领域(成本高收效低),老龄化必将激化矛盾。解决之道只有一个:慢病癌肿分流,向调、养分流。前提是人类要认识到自已的无知,一半的病靠科技也治不好,医与患都减少妄想妄为与妄作。改革的目的是医患皆安,前提是实事求是。“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外伤、感染类为“疾”;内伤系统类为“病”。病都是状态的表现,只有改变“态”才能治病。因人而异因时而调为“医”;以药厂+审批之药为基找病为“药”。“医”只知“药”而不调,是为传销。2/3的病是永远治不好的。1/3是人老化的病,长寿本身既是成就也是病因。1/3是病人长期因无知多欲而“作”的结果,世上不可能有一药而治,只能病去抽丝,咋来咋去。现代医学也不要“不知知”过度,从理论上承认才是自知之明。把这类病放在供给不足的医疗体系,等于全社会“无妄”。科技进步确实能降低成本提高疗效,但全球医疗体系是建立在垄断与牌照基石上的,本身就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快速转化。这也是自已找病而不知。结果反而是美国、北欧等所谓发达国家医疗财政先不堪重负。我国人口多财力有限,更不能走这条绝路。印度打破垄断与日本坚持东方医养值得借鉴。(在本书完稿的时候,刚好发生了新冠肺炎在欧美的流行,英、瑞等的“自然免疫”实在也是无法动员更多医疗资源。算一个验证吧。)
《军形第四》把“治未病”做了延伸,即在具体战场上先要预防疾病转移到更重要的病灶。比如典型的三阴病“肿瘤”与“糖尿病”。张仲景治病最关注脾胃战场,但是更强调先下药保住预计转移的下一个更重要战场。治消渴要死保的是“肾藏”,“故能自保”。“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不高明的医生总是想着投入更多的药力上前线,尽快消灭敌人于国门,“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如崇祯在关宁前线投入过多,反而脾胃不保,京城(肾藏)丢失。“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道理讲得明白了,却需要医生克服常人都有的人性弱点,主动示弱于病魔。争强好胜人皆有之,所以老子才会说“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医学何曾有自知之明,何曾能示弱于病毒、糖尿病、癌症,都是不知不可为而为之。1918年的流感还没有搞清楚,实际上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还没有特效药,其他如乙肝病毒、艾滋病病病毒,这么多年仍然无解。可笑的是,新冠肺炎杀到人间,立刻就有“某某德韦”自称神药。张仲景长沙抗疫治肺炎,所有的主方都是立足于先保下一个主战场脾胃与津液生成与循环(保阳气之本),再针对肺部用药,所谓药也没有一味能杀病毒,无非增强呼吸肌肉力量祛痰而已。只要能让病人保住脾胃,就能生成阳气津液,加上能祛痰,就能立于不败(不死)。立于不败,才能慢慢调养靠发汗以及肠道排除垃圾毒素而好转。
上医医国,下医医民之说,来自《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上以治民,下以治身”。治病如治国,治国如治病。治国治病就四个字:攘外安内。“攘外安内”的出处就是《伤寒论・太阳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汗吐下3法就是海陆空,用汤药为弹药攘外,把外邪给打出去;针灸之法是围三缺一,逼敌自退;五藏平衡是建立立体防线,敌无可攻;最高养生修养心神,就是王阳明打仗要诀“不动心”。
《内经》在上医医国上没忽悠华夏子孙。医国如医人侧重养而不是治。我们叫“汉人”,是因为汉朝以黄老之术养国为汉武帝打好了底子;在外国叫唐人是因为李家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唐玄宗更自封真人。只有武则天为了意识形态,主动推佛并引进景教(圣经教的一个非主流派)。
王阳明的名字也来自《内经》。他天生体弱,5岁改名“守仁丶字伯安。“仁”在《内经》的语境就是爱护身心,平和善意的状态。儒家引伸为爱别人。伯安就是大儿子要安康。他自号“阳明”,把余姚老家修练处叫阳明洞,“阳明”不是阴阳明白,而是《内经》的术语“阳明经”,对应胃气(胃功能)。张仲景治病就围着阳明胃做功课。王守仁是在学《内经》+《伤寒论》。真正学阴阳八卦是在龙场的山洞,他叫“玩易窝”。一出山洞就成诸葛亮了。修炼的成果是老来得子(之前不育,新婚逃出洞房找道士)。
举个糖尿病与大明的例子便于读者理解“战法”。崇祯与细菌入侵的清兵在山海关拼命,还要与病毒发作的流寇在陕西拼命,还被寄生虫东林党在东南吞噬赋税营养,这个病一命呜呼的时候,山海关精锐还在,东南财富还在,但北京没了。如果用糖尿病比喻,北京就是肾、山海关是肝、东南与中原是脾胃。虽然是三阴绝症,已经是六爻周期的最后一期,但张仲景认为天年未尽,仍然“可逆”。所以他发明了“四君子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补阳气去湿气,相当于精兵简政广纳贤才;还发明了“四逆散”(只烧干柴)去肝火,相当于压制内斗;最后用“四逆汤”(干姜、附子、炙甘草)回阳而生,类似强军健体。张仲景的打法,就是于谦对付瓦剌死守北京的战法。不寄希望于几味猛药能在长城沿线打死瓦剌病毒(因此也不必投入太多袁崇焕),这个长城就是肝,可以死缠烂打为抵抗病毒熬着时间;只要保住中原与江南补给包括援军陆续到来即可(脾胃),前提是保住肾藏死守北京,就死不了,死不了就能最终胜利。“四君子汤”的名字太好了,国难危亡之际,不就需要于谦+三杨这样的四君子补阳气去湿气吗,糖尿病等三阴病,只要先预防(治未病)不恶化到肾藏就能通过持久战赢得最后胜利。
《兵势第五》与《虚实第六》,很类似《素问》的“奇恒”“权衡”与“虚实”,都是阴阳变化。“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这些也都可以转换成《素问》语言。《行军第九》中还有养生=养军=必胜:“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这两篇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不能以药症思想当医生,更不能寄托希望于一剂而愈的神药。“势”就是态势+趋势,重在调整状态,引导趋势。比如中医常说的重病患者往往脾胃很差,如果调整到脾胃恢复,想吃东西了,有“胃气”就有“生气”。再比如,张仲景治疗糖尿病的四逆汤与四逆散,都在求“逆”其“势”。张仲景不仅以《六韬》《孙子》的建军哲学把之前零乱的方药进行归纳精简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治病方略,他还把人体从内到外分为六层战场,也就是六经,把每一层易出现的病症归纳逐次由表入里分析讲解(注意:是按身体分系统,不是按头痛脚痛分病)。六经统病、遣方用药,分明是一位战场统帅。另外,和《孙子兵法》的整体论、系统论一样,《伤寒论》同样不会把防疫与治病寄托于一味药或自恃兵强马壮穷兵黩武。中医的祛病原则不是对抗病邪,而是围三缺一给病邪以出路。节气+方药+针灸+情志的组合力量,来把病邪驱逐出人的系统内;病邪入里,仍然是用组合法驱逐+被迫药物杀敌。这和西方医学理论建立在某药杀某毒治某病完全不同。
糖尿病与痛风,中医认为都是脾虚+寒湿为主。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发病机理尚未完全掌握,因此只能“治表”:控制血糖与血嘌呤指标。从已有的医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
1、血糖、嘌呤都不是绝对的“垃圾”;分别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燃料)与蛋白质生成的原料。从元素分析角度,是“好”东西,为什么要用药控制呢?
2、血糖、嘌呤高都是“假”高,实际是不足。糖尿病人不能把血糖有效用于四肢才会厥冷;痛风病人不能把嘌呤有效用于脑、骨髓等深层组织反而沉淀在关节、肾脏。实际上就是“脾藏”的“运化”功能不足,对应往往是三焦的激素紊乱。
3、血糖、嘌呤的代谢都与肝脏与肾脏高度相关。最终也会危害这两个形脏。肾衰竭、肾脏堵死往往是死因。
4、血糖、嘌呤都涉及到“补救合成”,即将人体一部分分解加以利用,再合成血糖、嘌呤。肝糖消耗完细胞将分解脂肪来供应能量。人脑和神经细胞必须要糖来维持生存,必要时人体将分泌激素,把肌肉、皮肤甚至脏器摧毁,将其中蛋白质转化为糖,以维持生存。难民个个骨瘦如材就是这个原因。肝是体内从头合成嘌呤核苷酸的主要器官,不足时补救原料仍然是蛋白质。嘌呤补救合成是体内某些组织器官,例如脑、骨髓等由于缺乏只能通过腺苷激酶催化合成,外源性尿酸占20%,而内源性尿酸占80%。
5、血糖、嘌呤高低人体本身都能正常调节,都是激素作用。调节失效+恶性循环是两病的病因。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的缺乏,体内葡萄糖不能被利用,蛋白质和脂肪消耗增多,从而引起乏力、体重减轻;为了补偿糖分要多进食;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即为多饮、多食、多尿和体重减轻。糖尿病患者的多饮、多尿症状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呈正比。另外,患者吃得越多,血糖就越高,尿中失糖也越多,饥饿感就越厉害,恶性循环。痛风患者脑与骨髓越缺少嘌呤,就越会多分解蛋白质及多食入嘌呤,还是不能转化,更增加尿酸浓度,加大排尿,又减少嘌呤,也是恶性循环。
综合以上现代医学对两病的认识,不难看出:第一,西医确实治不好,是“不治之症”,只能终生服药维持,最终会死于原有病因+长期服药。第二,所有表现都对应脾藏与后文详述的三焦(内分泌)。
结论:三焦病最重要的治法是“调心”,再结合健脾。糖尿病与痛风都是可逆的。“心态”+“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是3大关键。张仲景《伤寒论》四逆汤和四逆散都是可逆。四君子汤才是治本。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句话既是对大型垄断药企一药治百病的批判,也是对后世中医积攒病例与药方,死记硬背照方抓药的批判。这样打仗治病都会失败,除非敌人不强,抓个小打个小股散兵游勇之类。因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孙思邈、李时珍,无论你千金方万金方,“孰能穷之哉!”。
“穷之”正是精准医疗的理想。目前的医学科技,最不能“穷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癌症。恶性肿瘤就是人们所说的癌症,它是100多种相关疾病的统称,目前是根据他们起始的器官或细胞类型来命名的。人类为什么会患上癌症?首先是有癌细胞,本身由自身细胞变异而来。目前医学认为导致细胞癌变的致病因子有3类:物理致病因子,如X射线、电离辐射;化学致癌因子,如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病毒致癌因子,如乙型肝炎病毒、疱疹病毒。前沿的基因科技认识到“p53”是一种可以阻止受损伤DNA复制的基因,如果p53失效,细胞就会获得像干细胞一样的永久生存性。癌细胞是生命的终点,干细胞是生命的起点。但是p53如何决定细胞向好或者坏转变呢?现代医学还发现几乎人人体内都会产生癌细胞,那为何有人得癌有人健康?
与病毒一样,如果人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能“穷之”,或者至少目前不能“穷之”,为什么现代医学的教科书敢于对病人轻动刀兵?首先人类应当认识到“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人的老化是必然,至于老化后得什么“癌”重要吗?年轻人以及中医所说“表”位置的癌相对容易治愈,如肺脏、肠道、胃、皮肤等,老年人与入里的癌,如三阴的肝、肾基本无治。这就是不可逆的“势”。对这类病人强行治疗,不如保守治疗,把资源用在更多保障末年的质量与死亡的尊严。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被认识到。另一个问题是,癌细胞一样依赖环境生长,比如怕氧,消耗能量多于正常细胞几倍之类。医学如果在内环境加大研究与疗法是否更有效?如果年轻人“阳气”尚存、津液能有效循环,轻易地动手术割掉甲状腺之类是否可取?本身所谓有效并非决定于手术,而是病人本身的状态;同时病因未除还会再生,加上切除部分再无系统协调功能。
总之,攻不在其因,守失其根本,这不正是孙子所谓“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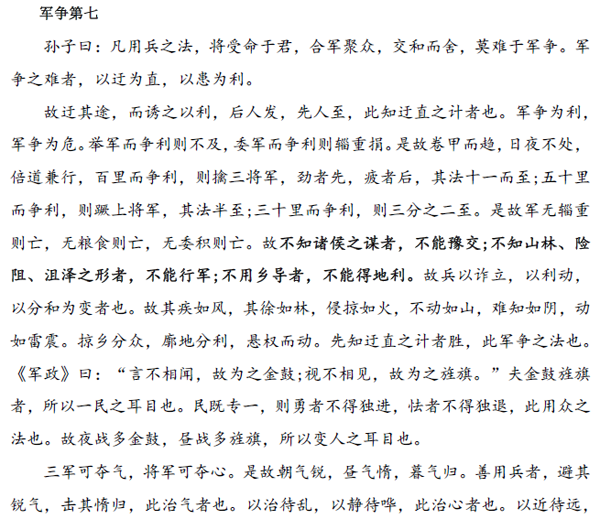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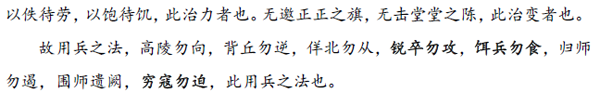
前篇《兵势第五》说要“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司命”的关键是“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病魔就没有智慧?当它抛出发烧、咳嗽、腹泻、疼痛等等让人感到很难受的“病症”时,正是医生要投入药力“军争”于表或里的时刻。“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如果医生把“表症”当病毒抛出的“饵兵”消灭了,结果会怎样?“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是用药之法,正是《素问》与《伤寒论》的引导病邪离开人体即胜的打法,而不用赶尽杀绝。因此在身体内被迫用“毒药”时,特别要求随着病症减轻立刻阶段性减药。这一点正是现代医学“指标”治病很难做到的。
“误诊率”是非常可怕,而又没有有效解决的一个医学老问题。国外有报道美国、以色列医生罢工期间,全国死亡率反而下降。以上各篇都要求减少“误诊率”,要从各个方面知己知彼,要把“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的各种要素通盘“庙算”,多么地不容易啊。所以孙子在结尾的第十三篇提供了答案:《用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左宗棠都强调缓进急攻,目标是“先知”,便是此意。“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类似中医的五运六气、望闻问切以及现代医学的各种诊断技术。重点是不能指标断病,一定要多类别互相验证。传统中医技术落后,现代医学强于也过于依赖设备仪器,而忽略了更多个性化的特征(地理、职业、社会关系等)。“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用间》强调“用间有五”,而且要“五间俱起”,全面考察: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这样才能成为伊尹、姜子牙一样的名医。
习主席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中医的复兴与回归,是生命哲学,绝不是排斥现代科技。恰恰相反,在哲学的指引下,中医应当勇于引进现代科技。比如随着检测手段与技术的进步,在多路径互相验证辩症思想指导下,完全可以对望闻问切进行革新;在机器人技术与数字成像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针灸完全可以实现智能化与精准化等等。对重要的药性,应当智能化精准检测,而不是依靠经验(烟草行业已经应用)。对于西药本身,也应当根据“君子用极”的指引,大胆使用,明确使用,但是应当坚持君臣佐使组合,对大寒类药物配合补精药物。“君子用极”本来就是《周易》《革》卦的思想,否则如何做到“小人革面”成为健康“新民”。如此,最高领导的支持与老百姓的需求,才能不被辜负。新中医不能靠古文与老先生的经验自立门户,那成了复古主义与经验医学,反而倒退了。
近代反中医的名人,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严复等一代人本身肩负引进科学与西学的使命,在落后中医垄断医疗阻挡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市场的创新时代,他们矫枉过正也不为过。梁启超自己被协和医院割错了肾并因此3年后死去,仍然为西医站台,正是用心良苦。笔者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化,非常理解传统产业对新兴技术的打压,尤其在垄断行业。新中医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凤凰涅槃,只有结合新科技把自己重生为比当下已经“传统”的医学更先进的“新医学”,才能复兴,复兴只能是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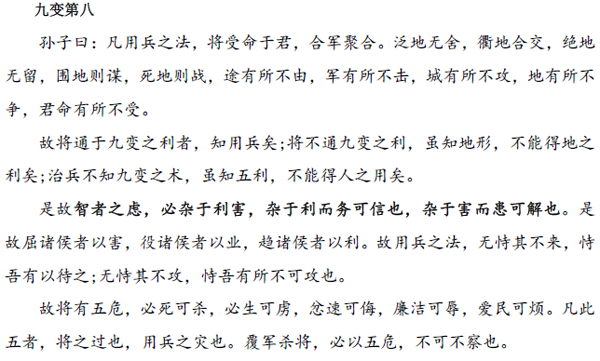
第二个道理很重要,所谓“通于九变”“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实际上这段内容与后面《行军第九》《地形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攻篇第十二》,都是讲天时、地利、人和“三螺旋”的。详见《素问新论:中医的逻辑》第二章更详细解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