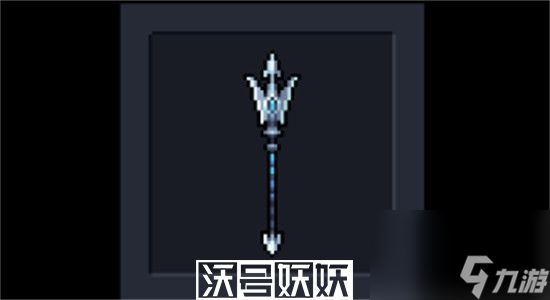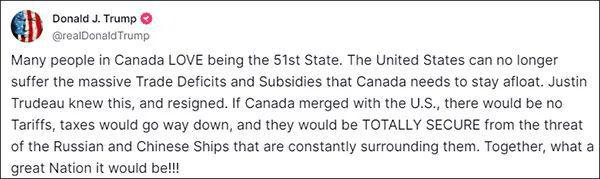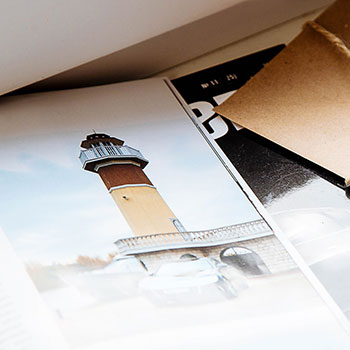前者创立于1970年,是业内公认的“医药一哥”,后者成立于2010年,是闪闪发亮的“药坛新星”。
2020年,两者总营收相差256.1亿元,那时的恒瑞一个季度赚的,比百济神州一年赚的还要多2倍。
随着2024年一季度的业绩公布,两者差距只剩6亿余元,而“新星”仍以同比超70%的增速狂奔,“老大哥”却才好不容易从水下探出头来,以不到10%的增速,缓慢爬坡。
按照分类,药品一般可以分为:创新药和仿制药。前者研发难度高、投入大、风险大,但利润也大,疗效也最新最好。后者则是等创新药专利过期以后,对原研药品进行仿制,安全和疗效差不多,但是价格更为低廉。
比如,《我不是药神》中白血病治疗药物——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2004年初入中国时原研药价格高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缺医少药的局面常常掣肘着国民,“三大神药”——土霉素、红药水和紫药水,三种有毒的药物被广泛使用。
直到改革开放,大量合资企业的进入,才让中国药企与国际接轨,通过仿制,完成对常见进口药的覆盖,并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仿制药的发展现状分析》提到,截至2017年底,中国有4000多家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其中90%以上都是仿制药企业。近17万个药品批号中,95%以上都是仿制药。
等着这个中国药科大学的高材生的,是厂里的账上只躺着8万利润,两任厂长都难以扭转,厂里面摆的,也只是几口大缸、几口大锅,用来罐装红药水和紫药水。
第一个被他盯上的是癌症化疗药物“依托泊苷”(代号“VP16”)——“在那个年代肿瘤患者很少,大型制药厂不会想到这一块,加上有技术壁垒,小厂也做不了。”
他花光了厂里所有的现金,买下了这款专利。随后推出的VP16胶囊,一炮而红,第二年药厂营收达到120万元,利润涨幅达1500%。
这一年的1月8日,恒瑞医药股价创下历史新高,最高涨至96.91。峰值之后,便是一路下滑,最低到了44.01,缩水一大半。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拉开了中国药品集采序幕,即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关机构组织“带量采购”,实行“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医院报量,企业自主参加、自主报价、以量换价。
过去药企是紧盯对手,不断通过技术研发、金牌销售,巩固自己的护城河。如今却是不论企业大小、龙头与否,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争夺集采的份额。
在2021年第五批国家药品集采中,恒瑞医药8个品种参与角逐,其中奥沙利铂、苯磺顺阿曲库铵、碘克沙醇、多西他赛等都是超30亿的大品种。
结果,恒瑞医药的重磅产品碘克沙醇注射液和格隆溴铵注射液,双双失标了。两者合占公司营收7.1%。
中标的产品,也出现了报价的严重失误。以中标量最大的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为例,根据财健道的报道,其报价158元,而另外两家中标对手,分别报价241.8元和343.8元,差距悬殊。
自 2018 年以来,公司涉及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仿制药共有 35 个品种,中选 22 个品种,
2022 年 11 月开始陆续执行的第七批集采涉及的 5 个药品,2022 年销售收入 9.8 亿元,
危急关头,拯救恒瑞的还是创始人孙飘扬。当时,已经“退休”1年多的他再度出山。迎接这位63岁老人的,却是更严峻的考验:
仿制药寒冬降临,“疗效差”、“低仿”的仿制药加快清理,有疗效、有议价能力的创新药重要性不断显现。
时至今日,恒瑞最拿得出手的,还是2020年销售额达48.9亿元的PD-1卡瑞利珠单抗,这也是目前国内创新药的销售峰值记录。
而百济神州的一款泽布替尼,2023年在全球狂揽10亿美元,成为国内首个“十亿美元分子”。今年营收更是有望整体超过恒瑞医药。
一种是自带项目的海归科学家+风投+CRO模式。比如百济神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施一公齐名的TOP级科学家创始人,再加高瓴等资本陪跑全程,如此得天独厚的基因是独一份。
一种是从仿制药起家,以仿促创,最终进军世界级药企,这条路来钱慢,但能走得远。恒瑞和大多数传统药企走的都是这条路。
孙飘扬口中的两个战略,恒瑞给出的答案是:历经10年,累计投资400亿元,研发出了16款创新药,另有90款余款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
国内临床研究管线最多的,正是恒瑞医药,是百济神州的两倍有余。哪怕是放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恒瑞也跻身全球管线药企之列。
根据阿基米德Biotech,今年,恒瑞医药年内上市创新药预计将超过20款,创新药销售占比有望达50%,未来2年将成恒瑞创新药上市密集阶段,预计有13款产品有望获批,包括抗肿瘤药物、术后镇痛药、治疗干眼症的眼科药物、自免和代谢领域的创新药等。
拿医保目录来说,虽然“推动创新药发展” “医药工程坚持创新引领”的文件出了不少,但据《财经》报道,2023年,扣除掉续约药品,在105款新入医保目录的药品中,首仿药仍是大头,占比44%。
十年内,国内的医药环境,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给恒瑞医药等一众以仿制药起家向创新药转型的传统药企,喘息调整的窗口期。
从其2023年业绩也能看到,恒瑞正慢慢消化集采的影响。经历2021年,2022年的营收和净利润双降后,恒瑞在2023年重回正增长,实现营业收入228.20亿元,其中,仿制药仍然贡献过半。
而这一年,恒瑞的研发投入为61.50 亿元,居于国内第二。由此,恒瑞可以继续靠着仿制药带来一半营收,以仿养创。
二是造了国人也买不起,欧美靠商业医保用得起高昂的创新药,中国依赖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创新药要进医保目录就得打骨折。
全世界创新药价格洼地不在仿制药大国印度,而是中国。“阿基米德Biotech”曾列举,司美格鲁肽印度定价为中国5倍,度普利尤单抗印度定价为中国3倍,奥希替尼印度定价为中国3倍。
作为全球药企最爱扫货的管线众多的“创新药超市”,恒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被先后有偿许可给美国、韩国、印度等公司。
出海经验不足的恒瑞,闹出BD(商务拓展)笑话,被中间商反手赚了几十倍(中间商花2500万美元从恒瑞买创新药,5个月后10亿美元卖出)。
5月16日,恒瑞医药以60亿美元的天价将其GLP-1系列管线打包出售给美国风投创建的Hercules公司,这场BD的总规模刷新了整个医药圈的眼界。除了首付款,恒瑞医药还将获得Hercules19.9%的股份,可以参与后续分成。这种形式在国内还是新的探索。
但紧接着的5月17日,又传来了PD-1联合疗法延迟在美上市的消息。PD-1产品推迟获批上市的原因有很多,诸多竞品在排队等上市是一大原因,对于恒瑞来说,产品“多而不精”是很大的问题。
近五年来,恒瑞海外营收一直在6、7亿元徘徊,占总营收比重未超过5%。2023年,恒瑞海外营收更是创下了5年内新低,只有6.17亿元,同比下滑20.93%。
如果十年周期内,恒瑞仍然未能靠创新药出海扭转局势,那“医药一哥”能否留在牌桌上,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