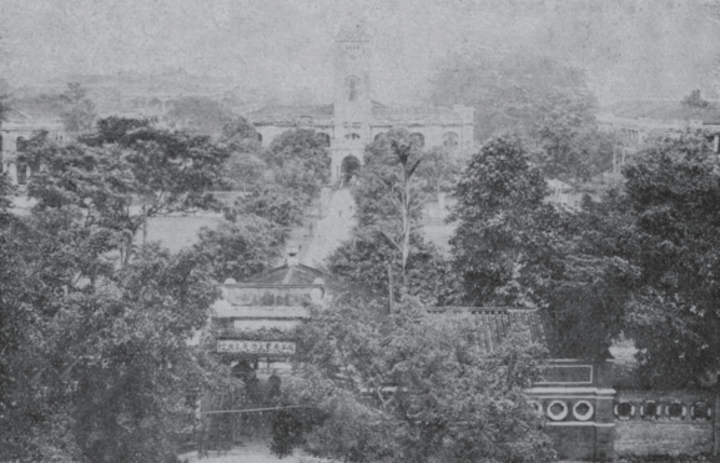人物档案:葛均波,中科院院士,著名心血管病学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他2000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九届青联常委。1990年公派赴德国留学。1993年,跟随其导师来到Essen大学医学院继续博士后研究,并于1995年任Essen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1999年4月回国。现为2002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973”项目子项目负责人,上海市医学发展重点基金研究课题首席专家。
今年4月1日,一则《中科院院士葛均波赴美航班上急救美国乘客》新闻被各大网站转载:葛均波在一个顶层学术会议上与美国心脏病学会进行高端交流,他乘坐从浦东飞往美国芝加哥的UA836航班,正闭目养精蓄锐,突然广播呼唤医生寻求帮助,葛均波即刻来到身体不适乘客的身边。经了解,该乘客一年前因房颤接受过心脏电复律治疗,起飞4小时左右出现胸闷、出冷汗等症状。他凭借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让该乘客吸氧,并利用飞机上仅有的酯类药物扩张其血管,同时积极协调乘务人员将患者从经济舱移至商务舱,以便平卧增加回心血量。经过初步诊治,该乘客病情暂缓,葛均波评估飞机不需要迫降或飞回。接下来十个小时中,他每隔一段时间即检查评估该患病乘客的病情,当这位乘客顺利抵达目的地时,人们纷纷对他翘起大拇指。他则淡然回答: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医生。
拿破仑有名言传世:不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小就有英雄主义情结的葛均波,尽管内敛低调,却也是不甘退居人后的。
留学第一年,葛均波即在《德国心脏病杂志》上发表《腔内超声准确性及可行性研究》。此后九年,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180多篇论文,主办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多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担任国际介入性心脏病新技术大会副主席、亚太介入心脏病学会主席,是国际冠心病协会顾问委员会的唯一华人,被评为欧洲心脏病学会和美国心脏病学院成员,1998年被评为世界500名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是世界医疗界熟悉的中国面孔。
1994年,当时还在德国读书的他,在国内第一次用一个镶有钻石的磨头以每分钟15万转的速度为病人打开了“生命通道”。这项被称作“高频旋磨术”的技术独步亚洲,位居国际先进行列,在心血管病诊断与治疗方面取得重大发现。
1999年葛均波作为“长江计划人才引进”后,一直在上海中山医院工作。他勇于开拓,不断引入新技术,为中山医院心脏介入诊治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地位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回国一个多月后,他促成了中山医院第一例心脏移植术,目前医院已成为国内施行此类手术的技术领先单位。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医院开创了上海地区第一条全天候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的“急症PTCA绿色通道”,成功救治数千例急症患者。
回国一年内,他实施了国内首例经桡动脉门诊冠状动脉造影,成功开展了国内首例高频旋磨术、国内首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上海首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上海首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术和上海首例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脑缺血。
对血管完全堵塞的冠心病患者,长期以来我国医务界毫无良策,病人都只得听天由命。他通过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的方法为血管阻塞的冠心病患者打通血管,使处于绝望中的病人重获新生。
葛均波发现了被称为“葛氏现象”的心肌桥“半月现象”,使心肌桥检出率大幅提高,被欧洲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评价为“应用血管内超声检测心肌桥的先驱”。他发明了可视冠脉激光成形术,改变了过去用X光照射的方法,采用超声和激光组合的方法治疗心血管狭窄,引起国际同行瞩目。
2005年10月,葛均波在经导管心血管治疗(TCT)会议上,首次通过卫星向远在美国华盛顿的主会场直播了上海中山医院心导管室的3个手术病例室间隔缺损、冠脉支架内再狭窄和左主干“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CTO)手术。手术圆满成功,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对医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2010年10月,葛均波又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该项手术应用心脏导管技术而无需开胸,为那些不能进行外科开胸手术的患者,特别是高龄患者带来了希望,成为我国心脏介入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葛均波主持下,在上海地区建立了急性心肌梗死抢救“绿色通道”,首创了24小时急症PTCA的先河。自“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已成功救治近千例急性心梗病人。
葛均波出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中至镇葛家崖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但父母崇尚知识,常常鼓励他好好学习,小学时他的聪慧就让他崭露头角。11岁时,一次骑自行车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后来被一位老中医治好。小小年纪的葛均波被老中医的医术深深折服,从此,当一名医生成了他一生的理想。
高中毕业,他考进山东省青岛医学院,从此治病救人成了他的立世之本。1990年他被公派留学德国,从此他在医学之路上从蹒跚学步到渐渐走向辉煌。在别人眼里他是是幸运的,而他自己心里明白:治一个人的病容易,救一个人的心则不容。他必须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只要生命还可珍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远倍受崇拜”美国爱默生的名言,是他饯行自己誓言的准则。
上世纪90年代末,葛均波开始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他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历经多年努力,研制成功“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降低了进口支架原来可能发生的支架血栓率,极大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并且由于国产化,大大降低了支架价格。由于其优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自2005年上市以来,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25%,平均每年超过8万名冠心病患者获益,每年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12亿元人民币,并出口国外,为国家创汇500多万美元。“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支架”的成功研制,大大提升了中国冠脉支架研发生产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回国至今,葛均波先后承担16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是国家“211”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国家“863”计划项目“药物涂层支架在冠心病应用的研制和开发”负责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子项目“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防治的基础研究炎症感染因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作用”负责人,上海市医学发展重点基金研究课题“疑难高危冠心病诊疗优化方案的研究”负责人,上海市科委发展基金项目“血管树突状细胞与动脉粥样硬化免疫机制的研究”负责人,并有国家教委课题、上海市曙光计划课题、特聘教授配套课题等,还负责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课题冠心病部分的科研工作。先后获得2003年上海市临床医学成果奖二等奖、2005年上海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05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5年中华医学奖二等奖、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1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鉴于葛均波在医疗领域的突出贡献,2011年12月9日,他当选为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后来还荣获第十二届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在葛院士的办公室,迎面就看到墙上挂着星云大师的墨宝:宽心。环顾四周,还有一幅:虚怀若谷。他指着沙发后面的一幅国画《花开富贵》告诉我:这是被我治愈的一个病人画的。从这些布置,看得出他的品位和人文修养。我不禁脱口而出:葛院士是否也是文学青年?他笑说:曾经也是,我还学过少有人知的弹拨乐秦琴,还曾经在东方电视台演出过。葛院士边说,边做出弹奏的姿势。
作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认为要在更高的平台上,利用专业知识来建言献策,从而把医疗行业做得更好。每年,他都要从专业角度提出四到五个提案,关注医疗改革、呼吁关注健康,倡议国家立法以及对科研经费的管理等等。今年,他又提出了在公共场所安置自动除颤仪及把高血糖高胆固醇测量放到基本医疗中等两项提案。提案被作为内部参考送达更高层,供决策参考。
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医患关系紧张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时,他强调重新建立良好有序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性。“文革”扭曲了一代人的价值观,社会上又对医生这个职业存在偏见。怎么消除医患之间的隔阂,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为此,他常常教育自己的学生,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要关爱病人,包容病人,争取病人的理解。他在学生时期就写过一篇文章“假如我是病人”,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来思考医疗对治病救人的善意本质。
对于网上纷纷扬扬的深圳孕妇被缝肛门案、看病右肾缺失案等,葛院士觉得无奈又痛心。无奈的是稍有医学常识的人一看便知漏洞百出,可媒体却推波助澜,让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把矛头指向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痛心的是医生都很忙,顾不上去反驳。所以他不想躲在高高的象牙塔里,而是常常会挤出时间,出现在一些科普讲座的现场。
常常有老乡拿了花生、鸡蛋来感谢他这位救命恩人。一次,有位河北的老人拿来两桶香油一定要他收下,实在没办法,他就对老人说,那我买下吧。葛院士说:这样做,只是为了心安,不想让患者感到难堪,不想让普通患者觉得我这个大专家缺乏人情味。我追问:如有病人一定要给红包怎么办?葛院士说:我会很巧妙地处理,要么等病人出院时打入他们的账户内,要么24小时内交给护士长登记。
葛院士的日程表总是排得很满,不是在机场,就是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这是常态。在别人眼里功成名就的大专家,也有常人之情。采访中葛院士直言:我不是专职干部,有时忙得也有点恼火,因为挤占了作为一名医生的看病时间。好多项目的评审、博士生的论文,这些都需要化时间。有时候在机场候机,还要打开文件。但这是责任,虽然也苦恼,因为总担心时间不够。作为医生,业务做不好,其他都是空的,我想把精力放在专业上。
他尽管忙,还是保证每星期二、四两天的手术。作为院士专家,他看好了无数的病人。许多被其他医院拒绝或者已被判定无望的病人,他都给看好了。说这些时,他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满意自得的笑容,那是对自己的肯定,是骄傲!
葛院士的儿子如今子承父业。有一天回家对他说:爸爸,今天有个病人要给我红包。他问儿子:你怎么处理?儿子说:我当然不会拿的,为了医生的尊严也不会收病人红包。他感到很欣慰,为儿子,也为整个医疗行业的主流价值观依然鲜明。